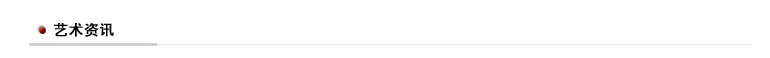|
生性敏感的我,不管是突然映入眼帘出于偶然,还是主动去观察源于必然,在我眼前出现的人和事,抓住我眼球,拨动我心弦,不管我愿不愿意,在心头挥之不去。摄影家杜伟的超现实摄影作品就这样悄然走进我心底。超现实主义艺术源于法国作家勃勒东(Andre Breton)发表于1924年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他在这篇宣言中写道:“超现实主义是人类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无意识活动。人们可以用无论是口头、书面还是其他方式来表达思想的这一真实过程——在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又没有任何美学和道德的成见时的思想之自由活动。”由此可见,这一艺术流派的哲学基础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他们看来,人的最真实的感觉只能在潜意识和梦幻当中。因此,人类的下意识活动、突发灵感、心理变态和梦幻世界,才是一切艺术驰骋的广阔天地。超现实主义摄影作品的画面虽然是“纪实”的,但只是用来物化摄影家头脑中瞬间意识运动的艺术符号。其创作趋向于“心理自由化”和纯直觉表现,通过自由联想,自由地、随意地、松散地、不受逻辑支配地进行创作,但又并非完全都是“想象的漫无边际,感情的无端跳跃,怪诞形象的杂乱堆积”。
摄影家杜伟用摄影镜头,用摄影语言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有秩序、还是无秩序的实物,按照自己的感受提炼出来,形成新的秩序,趣味的、荒诞的、清新的、混沌的……。那隐含的却又显性的艺术魅力,吸引着我,探究世界,探究作者,探究自我。他观察、审视世界的方式,存在的即为合理的,他以尊重、理智、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一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了认识世界,解开心中之谜,他身在其中,智在其外,跳出五行,探寻与他相合的东西。如《白大褂》的荒诞、《公交车》的趣味、《山道》的灵空、《泥瓦匠》的至酷、《小孩儿》的寻觅、《无题》的悠然入世、《沙发》的韵律、《城门》、《饭桌》和《烤地瓜》的完美构成,用摄影的语言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他的秩序,反映出他的主观情绪。
用亨利o卡蒂埃-布勒松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时时刻刻地观察事物,就像跳舞一样,在有意识和下意识之间摆动,突然地发现并抓取那些刹那间的、自然出现的、直观感觉的景物”,“与其说我是个摄影家,不如说我是个蚀刻家或水彩画家……我是一束等待着时机的神经,在景物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之中。突然拍摄,这是一种自然的快乐,是活动、时间与空间在某一时刻的集结”。
摄影家杜伟时时刻刻观察、审视身边的生活,刹那间出现的与他游离于另一个世界,摆脱了理性和意识,进入到梦境般的幻影,这种撞击与吻合融合在人世间说不清、道不明,及其微妙的情感之中,找到他释放思想、释放情怀的地方。那是一种发现,那是一种交流,那是一种愉悦。这种发现形成新的秩序,有构成,有韵律,有审美,有……;这种交流,形成新的语系,不用言语胜似语言,混沌中带着清醒,意会中有想象;这种愉悦,形成新的心境,认同中的肯定,拥抱后的抚摸,契合后的快感。
杜伟的摄影作品多数是形式大于内容,也有一部分作品形式即是内容。摄影技术技巧淹没在内容之中。
超现实主义摄影作品是很难用文字来诠释的,因为这类作品不是现实经验的记录,要用大家的共同经验去对超现实主义摄影作品作一番评论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我们也只能从它的句法及主张中去对超现实主义摄影作一可能是牵强附会的理解。超现实主义摄影既然不以记录现实为己任,那么其作品中的实物自然也不能是它们原本在客观世界中的原意,每一物体都是作为一种视觉图像符号而出现的,超现实主义摄影家用这些符号作词汇来造“影像句子”,而且这种“影像句子”很难能翻译成“语言句子”,这种句子中也往往会蕴含一种情绪、一缕诗情、一些感性和些许的政治意味,这些隐含的意味也正是超现实主义作品的艺术魅力所在。摄影家杜伟的摄影作品的魅力就在于无意识中的理性,冷峻中的温情。文如其人,风格即人。作品中对世界、对人类、对自我的思索和探寻,就是他内心真实的写照。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蓦然回首,奇幻美妙。
摄影家杜伟看完这篇文章,回邮件说,“如果说与我的思路有什么细微的差别的话,我觉得后面这几句(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蓦然回首,奇幻美妙。)似乎与我的心境不大吻合,它太诗意、太温情太能勾起万千思绪,而我的片子我个人的感觉是更多的清冷、更多的寒意。多于脑的思索,少于心的波澜。我觉得略去这几句可能更契合我的心境。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感受,每个人面对同一幅作品的感受都是不同的,胡老师是女性,感性的成份更多、更贴近生活。这毕竟是从胡老师的角度谈感受,还是由胡老师决定,这能更真实的反应出观者的内心感受。”(本文发表于2013年《艺术评论》) |